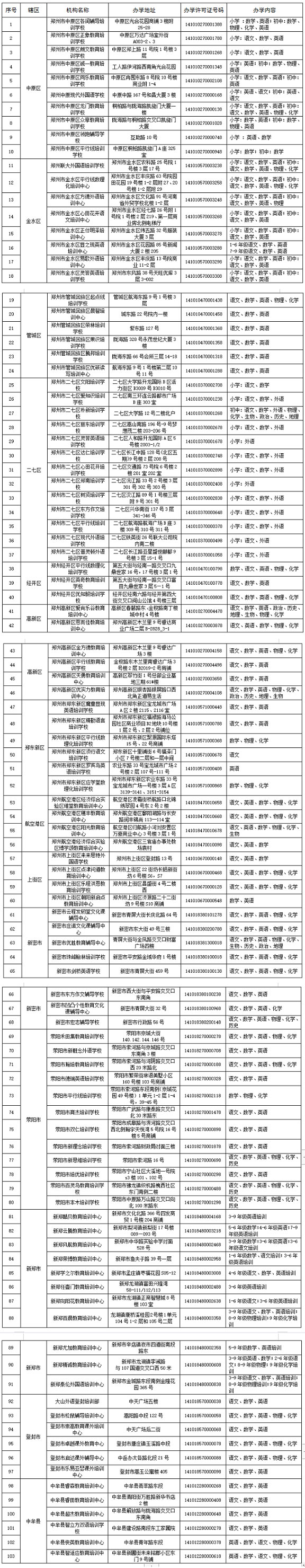没人敢再笑话广州人了
一个中午,和一位重庆籍朋友走在广州的街头,她突然说了一句话:“找工作的话,我再也不会离开广州,太喜欢广州了。”
她在好几个一线城市都有短期工作的经历,对比之下,在广州,“我不用穿得花里胡哨来表明我不是社会底层,广州人不在乎这个,他们尊重每一个人。”
读懂这座城市,你就会爱上她(视频来源:《广州,来了就不想走》)
这算是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。
一线城市我也都很熟悉,有的还生活了好几年。广州有千般好,最好的就是广州人从不把阶层地位当成一个重要的东西。对普通人而言就是一种温暖的感受,对能够进行抽象思维的人来说,这就叫平等。
下雨的广州也是温暖的(陈忧子 摄)
真诚的平等意识,是这座城市精神内核“道”之所在。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。它生成令人舒适的规则,营造温暖、融洽的社区生态,催生高效而谦和的政府,支持开放、交流的城市风气。
最难得的是,广州人的平等意识不是短期人为创造的,而是在数千年历史里一以贯之的,它根深叶茂。正因如此,同时生长着的,还有常居者的热爱,和路过者的不舍。
读懂这座城市,你就会爱上她。
普通话
前几天,我们有位记者写了关于河北邢台女孩萌萌被姐夫投毒的报道,我让她最后打电话去确认一个细节。
半天后,她愁眉苦脸地说,打了好几个电话,对面的人也愿意说话,但是都不说普通话,根本听不懂。
我有点惊讶。这种情况,我的经历更典型,但毕竟已经是9年前了。
2012年冬天,我去山东高密采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,感觉自己就像到了外国。
从高密出发,先要问怎么坐车,一路上问了路边五六个人,大家都朴实而热情,但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。摸到了车站,找到了车,在路上问车里的乘客到莫言家要在哪一站下车,大爷大妈们一样“热心到飞起”,但同样的,什么也没听懂。幸好路边挂着“莫言旧居”的指示牌,我迅速要求下车,照着方向进了村,一路问莫言家的院子在哪里,结果还是一样,听不懂,只能三步一问,跟着手指的方向走。
莫言先生的老父亲在家,老人很热情的给我倒了杯热水,我提了几个问题,他都来者不拒,问题还是同一个——听不懂,用广州话说就叫“鸡同鸭讲”。尴尬了一阵子,只好起身告辞。
有没有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?事情好像搞反了对不对?
本来应该是北方人担心来了广州听不懂广州话,甚至也听不懂广州人的普通话,但形势早就完全颠倒过来了。
广州人有最简单的快乐(郭嘉亮 摄)
20年前,广州人的普通话确实很差劲,经常有综艺节目,会故意模仿广州人说普通话,有一点喜剧效果,也有讽刺的意思。
新世纪初在北京上大学,有同学拿着一张纸,向我“请教”广州话(也叫粤语)的读法,我把上面的字读了一遍,才发现自己上当了。
上面写的是“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”,念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刚下完蛋的母鸡,同学随后哈哈大笑:“我母鸡啦!”
他没有恶意,只是觉得好玩。
但讽刺也罢,开玩笑也罢,人们都没有再往深一点想:为什么是广州人,乃至广东人,普通话口音总是被讽刺,或者被用来开玩笑?
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开口说普通话。倘若像上面的情形一样,坚持说方言,死活不说普通话,又怎么会落下话柄?
最现代的广州保持着最坚韧的传统(陈忧子 摄)
广州人那时也知道自己的普通话不好,电视台有专门学普通话的节目。片头先出来一个“444”,有人同时在念“细百细席细”,然后一阵哄堂大笑,再出来一个“666”,有人在念“楼百楼席楼”,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
这个节目以自嘲作为开头,目的却是鞭策。20年前的广州人说不好普通话,和今天一些北方城市不说普通话,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广州人学普通话的难度,显然比北方人学普通话要大得多,前者是系统性的陌生,而后者常常就是一个音调扭转的问题。但现在,用普通话在广州绝对畅通无阻,广州人无论老幼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反而到了许多北方城市,普通话根本不管用。
说不好和不肯说,区别在于态度,而态度反映的是文化。广州的文化,一直就是拿来主义的,“放出眼光,自己来拿”。
走在街头,处处都是轻松与信任(陈忧子 摄)
倒不是说北方人就没有拿来主义的精神,而是很多地方还不需要。这种需要,是由社会发展提出来的,对于广州而言,就是开放、交流。
广州历来就是万商云集之地,最大的需求就是畅达的交流。改革开放之后,普通话就成了畅达交流的必备工具,广州人就迅速接受并学好了普通话。
一开始是说不好,但架不住他们反复地说呀。说着说着,就没人敢再笑话广州人了。
“鸟语花香”
“鸟语花香”,是其它省份的人们形容广州时常用的词,带着戏谑成分。戏谑也无妨,但不能仅仅一笑了之,还应该了解它的来路。
“鸟语”是对广州话的戏称,因为它在外人听来太过难懂,易中天就说这是中国第二难懂的方言,第一位是闽南语。
然而之所以说难懂,是从以普通话作为好懂100分的角度说的。
改革开放以前,中国内部人口流动性很小,内贸规模也很小,日常里真正需要讲普通话的地方不多,各说各的,互不相干。所谓“好懂”的方言,只是因为它“长得”比较像普通话。比如东北话,以普通话为标准来衡量,显然就很好懂。
无处不在的笑容,叫醒广州每个角落(陈忧子 摄)
对于广州而言,国内贸易难度更大,因为北部横亘着南岭,交通受阻。相互交流很少,就意味着彼此对普通话的需求都不大。
广州以及珠三角平原各城市,一直是外向型的,它们有点像柏拉图在《斐多篇》里比喻的那样,各城市就像是围绕着池塘的一个个青蛙。人们因为地理决定,而向海求生,对外贸易一直是这个区域的历史特点。
近代史上,因为贸易往来、劳务输出乃至被贩卖出国(“卖猪仔”的由来),在国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,散布着数量庞大的广东籍华侨。这些人,作为不显眼的背景,却曾经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。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,背靠的就是无数广东籍华侨老乡;改革开放广东成为最前沿,设立特区,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与海外有大量的乡情联系,可以以此吸引投资。相当长时间里,星星般遍布世界的唐人街,主要通行广州话。
在这种情况下,广州话足以应付需求了。
工作或许繁忙,城市气质令人放松(陈忧子 摄)
虽然说是一个区域,但在近代以前,珠三角的经济、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广州一城。珠江西岸的佛山、珠海、中山、江门,华侨众多,全都属于广州统领之下的广府文化区域。
广州话,最早其实是秦朝大将任嚣率兵抵达岭南之后,中原话、百越语以及其它一些外来方言结合的产物。
秦朝太短命,任嚣出征不久,它就亡国了,任嚣随后在岭南病死,50万将士再无归期,就在副帅赵佗领导下定居下来,决心以此为家,努力与当地百越人融合,于是便形成可以沟通的语言——最早的广州话。
因此所谓“鸟语”,正是追求畅达交流的产物。它的特点不是难懂,而恰恰是好懂,易懂难懂,只看以什么为准绳。
对畅达交流的向往,始终是广州最重要的文化特质之一。而之所以向往畅达的交流,原因又在于这座城市从来不是静态的,总是有新的外来元素不断地闯入。
自汉朝以来,广州就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,广州的贸易通达波斯湾、东非和欧洲,航路全长14000公里,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。
与此相应,世界各地的商人也频繁活动在广州城,“舟舶继路,商使交属”。这座城市里就不但南腔北调,而且还“东腔西调”了。唐代长安,繁华成一时之盛,各国使节、商人、学者、学生云集上国首都,而在广州,外商往来则是历史常态。
在近代以前,商业没有成为殖民主义炮舰的前驱的时候,它就是一种比较单纯、善意、平等的交流。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,彼此怎样表达善意呢?送上一捧鲜花,就人人都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善意。
这就是所谓“花香”。
广州人爱花是全国有名的,但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这里气候适宜,四季有花,更在于花对广州人而言有特殊的功能——它是一种普世性的、无声的语言。
无花不广州(何易成 摄)
一般情况下,越是常见的东西,就越不会自觉地喜欢,比如只有城市里的人们才会向往田园阡陌之美,身在其中的农民对此根本毫无知觉。没有丝毫贬低之意,只是客观地举例,云南更适宜鲜花生长,也有更多种类的花,但在国内市场连通之前,当地的鲜花主要是用来做菜的,因为它不承担其它的功能。
而在广州,不同语言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,要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共生共处,必须借助各种最容易理解的符号,来传达话语和情感。鲜花就是一种最简洁的、最大公约数的符号,花是人类共同的审美,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语言功能,成为一种交流的媒介。
平等与善意,不依赖语言(卢文 摄)
广州人的鲜花是用来表达的,用来欣赏的,像一种礼器,也像一种文玩,而不是生活实用器。
由此观之,则“鸟语花香”,并没什么不好。
一口通商的繁华
我大学时的班级,是由每个省市各两名同学组成的,分布均匀,天南地北,所以同学们对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历史文化都饶有兴致。
一位同学对我说,你们广东,历史上就是蛮荒之地。我当然不能苟同,讲了秦朝建立任嚣城(广州),以及汉唐宋元贸易之盛,但他不相信,也没有兴趣听。
这也难怪。
历史上,南岭阻隔的不仅仅是商贸通路,它还阻隔了其它两种重要的东西。
一是阻隔了政治与战争。
政治中心权力的争斗与变幻,中原腹地的逐鹿与杀伐,很少波及岭南地区,而历史总是倾向于浓墨重彩地记载政治与战争的。
中原的逐鹿与杀伐,只存在于棋盘上(陈忧子 摄)
二是阻隔了岭南士子的求学进阶之路。
因为参加考试非常艰难,而岭南贸易繁荣又提供了科举之外的替代性出路,岭南就形成了一种远儒传统,而中国的正史,是以儒家精神为核心书写的。
岭南与国家政治文化中心联系不易,最经常发生的往来,就是一些贬谪的士人、流放的囚徒,悲悲切切地南来,写下一些担心自己水土不服、愁病而死的诗文。
这些悲观失意者,是有条件向中原讲述岭南情状的人,因为其中很多人最后还要回去。然而身在广东的时候,不是贬谪之人,就是戴罪之身,心情糟糕至极,自然不会把岭南写得春光明媚,一派欣欣向荣,而是动辄蛇虫遍布、烟瘴横生。说白了就是身在异乡,环境不熟,水土不服,否则岭南人民,怎么世代生存下来呢?
但这些诗文,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对岭南的印象,人们也并不多加思考。
常居者的热爱(陈忧子 摄)
一如历史记载的不重视一样,这些情况对于我那位同学而言也不重要。他只承认清朝乾隆以来,广州一口通商之后,造就了独特的贸易繁荣,广东才摆脱了蛮荒处境。
那我又问,为什么当时朝廷指定一口通商的的是广州,而不是你的家乡?
他的家乡在长江中游,江边的一个地级市。
“那怎么能比呢?你们广州一向以来就是对外通商的。”
鲜花勾勒的广州(卢文 摄)
这就对了,问题又绕回来了:正是因为有基础,有传统,有历史。
汉代,广州已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;唐代,已是世界著名商埠,与50多国有经济文化往来;宋时,广州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第一大港;到了元代,已与14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。“广州通海夷道”,自古“雄藩夷之宝货,冠吴越之繁华”。
一口通商,其实正是繁华的结果,而不是繁华的原因。
“南风窗”
一口通商确实也造成了新的事实,那就是,近代史聚焦到了广州,一贯被正史所忽视的岭南地区,顺势闯入了近代历史的中心。
从那以后,岭南、广州就再也无法被写历史的人忽视。事情是这样的:
英国工业以纺织业起家,它的棉衣、毛衣在岭南湿热之地卖不出去,年年逆差,就向中国输入鸦片来平衡贸易,鸦片荼毒生灵,于是便有了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到广东,组织禁烟,英国便发动了鸦片战争。
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界,近代史的开端。
广州人虽然重视商业,为各国商人创造了最好的生意环境,为了商业往来甚至创造了“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”——洋泾浜英语(又叫广东英语),但在民族大义面前,也绝不含糊。广州人最早挺身而起抵抗帝国主义侵略,三元里抗英,震惊中外。而在《南京条约》签订之后,为了抗拒英国人入城,从1843年到1849年,广州人民坚持了7年的战斗,取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。
第一次鸦片战争实现了英国人的目的,那就是把贸易前沿往北推进,好把毛衣棉衣卖出去,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这些良港,都按照条约要求开放。上海从一个县城,变成了开放的中心,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十里洋场,亚洲第一大城市。
而这时的广州,已经开始承担起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历史使命。
一架桥的历史,藏着一座城的故事。图为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广州海珠桥(资料照片,新华社记者 黄鉴秋 摄)
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,就是因为来到广州,看到国家落后的实情,编写了《四洲志》,后来又把资料交给魏源,嘱咐后者编写了著名的《海国图志》。
洪秀全从这里出发,接触基督教,进行反清起义的思想准备。
康有为在此讲学,蓄积声望,收下弟子梁启超,其后一起北上,维新变法。
孙中山以此为起点,拉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,并且以此为大本营,生命不息,革命不止。
年幼的中国共产党,在这里公开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“中共三大”,因为这里是当时唯一可以“合法革命”地方,随后,革命先辈们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浪潮。
2021年6月20日,广州,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
新中国成立以后,面临西方封锁,仍然几乎年年不辍地在广州举办广交会。
改革开放,广州同样是前锋,体制改革过五关斩六将,而中国大陆最早的流行文化,也在广州发端。
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,以香港、澳门、广州、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,广州从综合地位上看,依然举足轻重。
贸易的往来,海外情谊的联系,新观念、新知识的输入,在广州话里被形容为“南风窗”。
高塔瞭望,熏风南来(黎建锋 摄)
广州,就一直是中国的“南风窗”。有这扇窗,就总有意外的惊喜。
90后画家西茜是我的朋友,去年11月的某天,她说年底要来广州。“哥哥你能不能带我去吃地道的粤菜?广州的东西很好吃。”
我说:“可以啊,广州可远远不止东西好吃呢。”
作者 | 南风窗新媒体主编 李少威